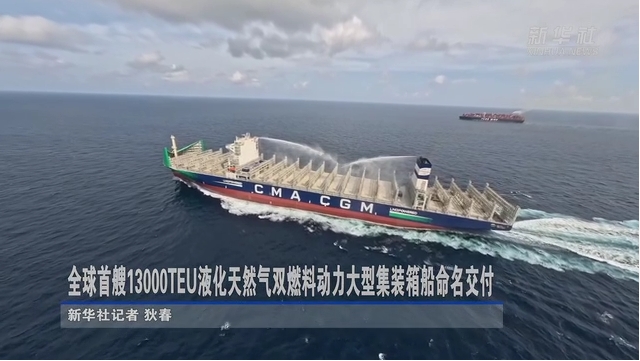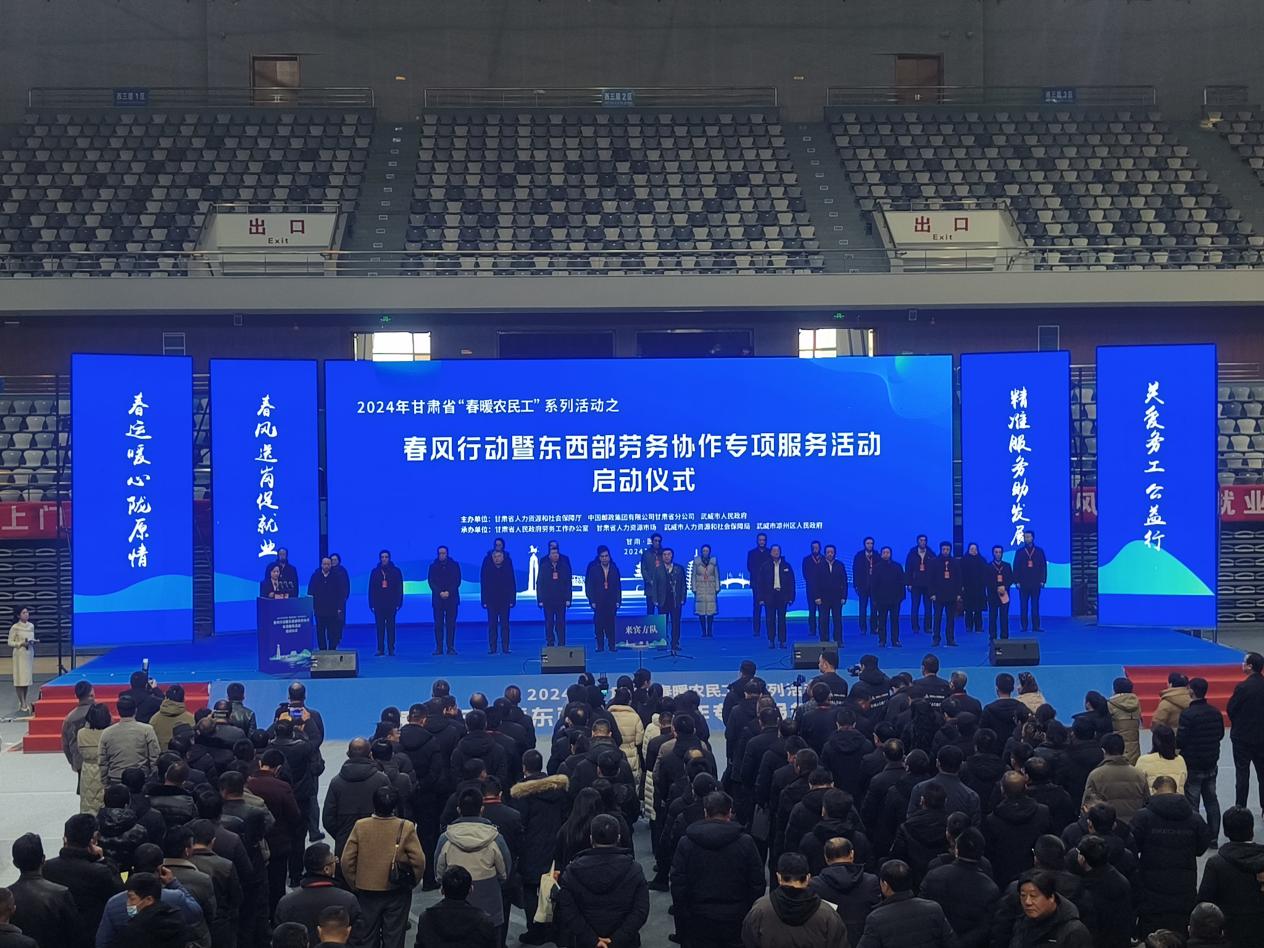■杨维勇‖甘肃
我的老家在会宁县头寨镇双坪村樊家湾社,樊家湾一名从何而来,已无从考证,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没有住过一户姓樊的人家,问我长一辈的人也不知道有过姓樊的人。我出生的地方叫挖窑湾,是樊家湾的一角。从挖窑湾的土窑洞里呱呱坠地,一直到学龄时背着一个装书装馍馍的布紁紁(布袋),提着一个装水的亮瓶(空酒甁)小学毕业,在故乡生话了十来年。
上中学便从樊家湾走出来,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头寨中学住校上学,一周回家背一次馍馍、炒面和咸菜之类,以备住校期间的早、晚饭之需。每月还要准备几斤白面和几角钱交到学校的灶上,这样中午才能在食堂打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吃。
之后又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靖远师范上学,好在师范就读期间,学费、伙食、住宿国家全包,不用再担心温饱问题。每月领饭票时还能在食堂管理员那里领到几块零花钱,用于买文具、肥皂、牙膏之类。
再之后又到几千公里远的外地从军吃粮,开启又一段人生,从此告别了故土。

远离家乡已四十余年,在外思乡,心绪万千,乡愁浓浓。家乡的一些小地名也变得逐渐模糊起来,有的虽能想起地貌,但想不起叫什么。
依稀记得老家樊家湾周围有很多叫湾的小地方,如挖窑湾、隔岘湾、上湾、小湾、庙湾、叠叠湾、阳坡湾、簸箕湾、老虎湾、臭老虎湾、黑鹰湾、黑窑湾、涧沟湾、马圈湾、回回湾、河西湾等等。
除了叫湾的地方,就是山了。如护山。它是我家老庄子三间窑洞和同族几家住宅的靠山,山后是我们家的祖坟。当初几家人约定:不允许放牧牛羊牲畜到此山吃草,因为大家平时都有保护意识,山上的植被要比其它地方茂盛一些,故名护山;
老爷山。因山腰有据说是清朝年间建的双粮神庙而得名,早年间比较破败,有个老先生曾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认字。近些年经过不断翻修扩建,山门耸立,殿堂雄伟,红砖青瓦,琉璃彩绘,雕梁画栋,飞檐走壁,规模比以前大了很多。庙的周围裁种了不少松柏,十分茂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过年过节时香火十分旺盛。不知什么时候起又把此山改叫前明山,把庙改叫万圣寺。算是湾里最宏伟的建筑和最热闹的一处地方;
堡子山。因山顶似方似圆如一高高隆起的堡子而得名,也有传说很早以前当地的富户为防匪患,有在此山顶筑堡子的设想。山顶方圆约有四五十亩地,山后乱庄村的人曾在山上耕种过胡麻和谷子一类的农作物。往往是广种薄收,天旱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后逐渐荒芜;
老虎山。传说很早很早以前此山上出现过老虎,因此而得名。此山早年间经常有狐狸和野狼出没,小时侯曾亲眼目睹过在山上放的羊被狼叼走,村里的鸡被狐狸吃掉,人们眼睁睁的看着,很是无助。曾有一住户把偷鸡的狐狸堵在鸡窝里,栓上绳子在村里的打麦场上玩,不久后又放归山野。
骨茬山。是最高的一座山,在方圆百公里内算是一座名山,从山顶到山脚落差上千米。民间传说山上有一处深不可测的洞,有蜈蚣在洞内修炼成精。姑且不论传说真假,但听着蜈蚣二字便觉得有点毛骨怵然,很是吓人。这座山的周围夏季容易下冰雹,为防冰雹毁坏庄稼,曾在山顶设有人工防雹点,预测有冰雹时,值班人员就向空中的云层发射专用炮弹,将乌云驱散。山上有近百亩地,牛家河村的人在山顶种过粮,骨茬山的山名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硬山山。山体高大陡峭,是老虎山的南面一侧,其实是阴山屲,但湾里人叫硬山屲。还有不少小山包已记不起叫什么名字了。
湾里有通向四面八方的小路。从叠叠湾出去便是走王家岔和塬边的路了。当时塬边设有人民公社,后合并改建乡镇撤销。儿时湾里没有通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还是定量供应,快用完时几个玩伴就拎着空酒瓶去塬边后面的泉坪商店灌煤油。这条路上山大沟深,不时有狼和狐狸出没,小时候不结伴单人不敢行。还有叠叠湾后面要经过的一条很深很陡的涧沟,十分难行,只是走的人不是很多。记得文革期间刮“十二级台风”时,父亲不知何故在塬边公社的批斗会上被突然纠斗,听得一声喊打,只见一顿棍棒、麻绳、皮鞭飞舞,来回抽打在父亲身上,顿时皮开肉绽,便体鳞伤,当场昏了过去,残不忍睹。不太懂事的我当时是去看然闹的,不想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大气也不敢出一声。批斗会后四叔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借用一辆小木推车把父亲从会场扶上车子,经塬边北坡的猴儿牙岔、王家岔涧沟、叠叠湾一路颠簸推到家。当时也没有药,不知该怎么办,母亲只好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打碎在碗里,捞出蛋清敷在父亲被打的伤口上。过了几天,伤口全变成了紫青色。父亲忍着疼痛,在家里的土炕上静静躺了一个多月才勉强恢复。好在我们家是贫农出身,属于依靠的力量,政历清白,再未批斗。落实政策时说被人冤枉的,父亲和工作组的人吵得很厉害,说既然是错误纠斗,要求召开同样规模的大会,当众平反,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县上和公社的联合工作组又来了两次,叫了和父亲关系比较好的乡亲同事一起做工作,父亲才勉强同意,随即平反昭雪。从此,我对父亲更加敬重!他1米8的个头,很是伟岸。声如洪钟,行事果断,走路如风。解放前村里有一大户人家被派兵役,不愿意去,便和父亲商量,许以十石(担)小麦和少许杂粮作为代价(当时十石小麦据说有好几千斤),换他去服兵役。这样家里就不再为吃粮发愁,父亲就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邓宝珊部当兵服役。一年多后全国解放,被西北野战军收编,又成了解放军的一员。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五十年代著名的百川渠会战和引洮工程,在引洮工程中因山体塌方救人受伤,受到工程指挥部的表彰。我想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冲击,可能是因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事而起。他教诲我们时有一句口头禅:“将小、将小,天下走了”。意思是不论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谦虚谨慎。父亲说他一生无罕事,一辈子凭良心做人。年届八旬走完一生,得以善终!
从庙湾子出去便是走对坝子、乱庄、牛岔、大湾、小白崖、阳屲、五.一林场的路。乱庄是当年双坪大队部的所在地,建有几间平房和一个小商店,还有一所学校,是当年双坪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也叫高小。全大队六个社的小学生,在念完四年级后都要来这里再读两年,才算是小学毕业。走这条路的人比较多,相对好走一些,姑舅家也在乱庄,在这条路上去高小读书上课,偶尔走亲戚,或到大队部的商店买东西,来来回回一直走到高小毕业。
从簸箕湾的上豁岘出去,左手可去双窖坪、下阳山。右手便是去李家圈、蛤蟆沟、老油坊、罗家湾、童家湾、路长湾的路。因李家圈有个最早建立的初级小学,加上天旱时人们去蛤蟆沟取泉水吃,平时赶牛羊骡马去沟里饮水,走的人也算是比较多的一条路。李家圈小学院内有两丛玫瑰花,小时候管它叫刺梅花,长的十分茂盛,整丛花围一圈有五六米,比成年人还高出一截,每当盛花期,鲜艳夺目,香气四溢,十分清新。初小四年从这条路上早出晚归,蹦蹦跳跳,乐此不疲。
从硬山屲沿半山腰人工开挖的简易土路直行至连接老虎山和谷茬山的一处叫铁门框的豁岘出去,便是走史家湾、阳山、丁家嘴,马家堡的路。这是一条真正走出湾里和大山的路了。沿着这条路再向外延伸,南北走向便是兰宜公路即309国道,东西走向是会宁县郭城镇至定西市馋口镇的公路。湾里的人们平时赶集、购买生活用品都要到山外二十多公里的头寨子镇去,是人来人往最多的一条路。七八十年代手扶拖拉机和小车就能通行,经过这些年政策性的不断修修补补和乡邻们的精心维护,大车也能通行了。虽行车时尘土飞扬,也算是一条湾里通向山外的准乡村公路。
从河西湾出去有一条路是走黑庄和头寨子镇的路。七十年代闹饥荒吃回销粮时,湾里的人去黑庄粮站打粮,为了打截路、省时间,背着沉甸甸的粮袋,走的就是这条路。记得经过的小路边有一户王姓人家的水窖,平时放有水桶。打粮回来走的都是上坡路,经过此处,正值炎阳高照,人困马乏,个个汗流夹背,口干舌噪。于是大家都要停下歇一会,并从窖里打上来一桶水,就着水桶轮流喝,十分清凉解渴。这是一条典型的羊肠小道,估计现在走的人很少了。
还有一条出山的路是一条长长的沟。沟的两旁盛产一种叫黑柴的植物。物资匮乏的年代,有年长的人不顾危险,在悬崖陡坡处把黑柴挖下来,背到自家门前晒干。之后在地上刨个深坑,把黑柴点着烧制成块。平时储存起来,用时取一小块砸碎,放进盆子里浇水浸泡,颜色黑糊糊的,很是稀罕。湾里人管它叫灰水,乡邻间以物易物或馈赠,和面、蒸馍、烙饼子时当碱用。沟里有泉水,泉眼汨出的全是咸水,这种咸水能熬制土盐巴,所以把这条沟叫盐沟。记得湾里曾有一老太太在此熬过土盐,她在沟底筑了个小坝,把泉里流出的水聚在一起,架起两口大铁锅,把咸水倒在里面熬,很是费时。土盐熬成结晶状,晾晒在地上,雪白雪白的,很好看。那时不允许公开买卖,湾里的人也经常悄悄拿着粮食之类去兑换,供调味用,但调在饭菜里吃起来味道却有点发苦、发涩。这条沟有数十公里长,从沟里走出去就是黑庄村和头寨镇了。当年去头寨中学上学报名时,我背着铺盖卷,在老父亲引领下走的就是这条沟。只走过一两次,沟两侧全是悬崖,有老鹰和燕子在陡壁处筑巢,抬头眺望,犹见一线天。道路泥泞,特别难走,胆子小的人一个人是不敢轻易走这条路的。听说早年间有人在这条沟里迷过路,差点走不出来。
除了能叫上名的路外,湾里还有数不清的羊肠小道,也是儿时爬山放羊,拔草铲柴,雨天抓山鸡娃,追野兔,拣鸟蛋,摘沙葱时脚下经常丈量的地方。正应了鲁迅先生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樊家湾还有一景,就是水窖特别多,每家门前都有两三眼水窑,也是西北干旱地区的特色。这里降雨量少,靠天吃饭,夏秋季节天阴下雨时人们将雨水集在窖里,冬春季天下雪了把积雪倒在窖里,解决了这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人畜饮水的问题。别看小小的水窖,它里面装的不仅仅是水,而是老祖宗的智慧和创造。窖的形状有点象彩陶罐,窖口和窖底小,中间大,宽约数米,深好几丈。水储在里面不管多长时间也不会变质,也不渗不漏,十分奇特。挖水窖还是个技术活,有一套繁杂的程序,十分辛苦,一般人干不了。要专门请有此技艺的人打窖,从开挖到打成一眼窖要好几个月时间。现在随着钢筋水泥和大型塑料储水罐的使用,已经很少有人打土水窖了,但很早以前打的水窖还在使用。估计再过若干年,古老的打水窖手艺会成为非遗传承相目。
樊家湾这些年走出了不少大学生,更有硕士、博士和教授,亦不乏达官显贵。他们从山前的小路跳出铁门框走向外面的世界,从学、从农、从工、从商、从医、从教、从政、从军,打拼生活,成家立业,也为樊家湾争光添彩。
尽管这些年新农村建设大多数人移民搬走了,但仍然有人执着的坚守在这里,或因深爱着这片土地,或因故土难离。尤其每年清明节前,来湾里祭祖上坟的人络绎不绝,宁静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
虽然自然条件艰苦,我亦视樊家湾为风水宝地。她四周被群山环抱,每当下雨雾绕山头,瑞蔼霏霏,令人神清气爽。雨后彩虹当空,犹如仙境一般,美不胜收。
湾里的低洼处即山脚下是一家一户的良田,每当山间传来嘎啦鸡(当地的一种野山鸡)的第一声欢叫,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杏花、桃花、梨花竞相开放,人们开始耕种,遍野的花草也从地下探出头来,沐浴着属于它们的那一抹阳光,到处生机盎然。
夏天庄稼地里绿油油一片,站在田埂边,仿佛能听到农作物的拔节声。偶尔一阵微风掠过,麦浪滚滚,似片片银帆来回摆渡。
收获的季节,熟透的谷子糜子笑弯了腰,低头向辛勤耕作的人们行着厚礼。秧杆已枯萎的洋芋(土豆)被一窝一窝挖出,散落在田间,满地金黄。
隆冬来临,湾里被大雪覆盖,到处银装素裹。一切沉寂下来,风景这边独好。
当夕阳夕下,湾里升起袅袅炊烟,远远就能闻到农家饭菜的香味,更有一番景致,让人流连忘返。
樊家湾象个聚宝盆一样,用温柔的怀抱,无私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子民。
她还有一副天然的铁门框,镶嵌在进湾的必经要道上,连同湾里的乡亲,日夜守护着这里的安宁。而一旦有学子金榜题名或有人事业有成,则寓意跨过了“铁门框”,犹如鲤鱼跃龙门,预示着命运的改写。湾里人总要庆祝一番。
走过千山万水,游历江河湖海,外面的世界故然精彩,我仍深爱着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樊家湾,因为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作者简介


杨维勇,甘肃会宁人,大学本科学历,22载军旅生涯,上校军衔。退役后从事新闻工作,记者。喜欢体育、音乐、书法、写作。其在军、地撰写的新闻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先后发表在解放军报、解放军后勤文艺、中国青年报、青海日报、人民军队报、质量服务报、科技鑫报、大西北网等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