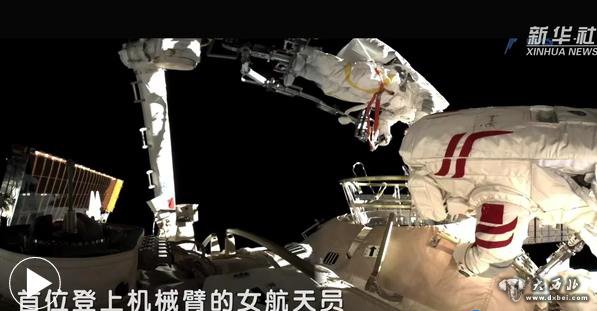秦文化的发现和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基本同步。30年代国立北平研究院为了探索周、秦二族文化派人赴陕西调查,苏秉琦先生主持发掘了宝鸡斗鸡台的屈肢葬墓,首先接触到了秦文化,虽然没有直接命名,但已将它与其他性质的文化区分开来。这是严格意义上秦文化考古工作的开始[1]。
50年代至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西安半坡、长安客省庄、宝鸡福临堡、宝鸡秦家沟等地发掘了一些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秦墓,已基本能够理顺它们之间的年代先后关系。此外,还调查了雍城、栎阳、咸阳故址,确定其地望,并作了一些试掘。这一阶段属于资料的积累时期[2]。
70年代至80年代初,重大发现接踵而至:兵马俑坑举世瞩目;云梦秦简令学界沸腾;雍城陵园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秦国都城的真面目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开始显山露水。中小型墓葬的发掘全面铺开,雍城南郊高庄和八旗屯墓地尤为重要,为后来秦墓的编年工作奠定了基础[3]。
80年代研究成果累累:一些学者开始总结秦文化的特征;墓葬分期亦由粗到细;人们为屈肢葬的含义争论不休;关于秦文化渊源的讨论也变得异常激烈,并导致了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西周秦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掘[4]。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历经十载,最后“揭椁”时,新闻媒体鼓噪一时,但留给大家的是大量文物被盗的无限缺憾。整个80年代,发现的狂热已经让位于冷静的理性思考。
90年代,研究趋向专门化,在金文、陶文、城市、陵墓方面相继有专著问世。田野工作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了宝鸡益门村秦墓的发现[5];在陇县店子村和咸阳任家嘴、塔尔坡发掘的秦墓[6],除了可以印证以前的分期,还为分类分区提供了依据。考古报告的完善,使个案研究成为可能。近年西安北郊相家巷有大宗秦代封泥面世[7],可望在秦代职官、地理研究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
二当前秦文化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
1、关于“秦文化”的概念问题
这里所说的“秦文化”,指存在于一定时间、分布于一定空间,主要由秦族秦人及相关人群创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包括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总和及其所反映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
秦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如果把起源阶段包括在内,其年代上限或可追溯到商代晚期;如果把消亡阶段也考虑进去,其年代下限或可推迟到西汉早期。秦文化的分布区域有一个自西向东、自小向大的发展过程:西周时局限在渭河上游、陇山以西的河谷地带,春秋时扩散至整个关中地区,战国中晚期以后开始遍布全国。
秦文化和秦族秦人有着复杂的辨证关系。并非所有秦人使用的文化都属于秦文化,例如战国末年以后,关中秦民中有的迫于苛政亡入周边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混居在当地人中间,“以夷变夏”,使用着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和关中有很大区别,如同汉武帝时投靠匈奴的李陵已“椎髻左衽”。有些非秦人使用的文化反倒可以归入秦文化的范畴,如在陕西户县宋村和南关发现的春秋早期酆国王室墓葬,青铜器与同时期陇县边家庄秦宗族墓地所出酷似,属于同一文化。因此,不能简单认为秦文化就是秦族秦人文化。
界定秦文化的首要标准是文化特征,而非时间、空间、国别。秦国建立于公元前770年,灭亡于公元前207年,但秦文化并不与之同步。秦国版图不断扩大,在新占领区往往既有秦人、又有本地居民,遗存面貌也驳杂不一。例如公元前237年秦灭韩后,郑州一带划归三川郡,但那里既有出釜、盆、罐的秦人墓,又有出鼎、盒、壶的韩人墓,文化性质判然有别。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秦文化就是秦国文化。
70年代俞伟超先生曾对秦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加以概括,秦文化概念的提出则是考古学文化本体论日益明朗化的结果,它继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的讨论之后,必将随着考古学理论的进步而发展。
2、秦文化的分期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必须建立在典型遗址分期的基础上。50-60年代,田野工作刚刚展开,材料不足,秦文化的全面分期还无从谈起。70年代,凤翔雍城南郊几处规模较大的秦中小型墓群被清理,使秦墓的编年成为现实。80年代,长期在雍城工作的尚志儒先生根据随葬品组合和形态把秦国小型墓分为7期,并综述了各期特点[8]。叶小燕先生把全国范围的秦墓分为5个阶段,并论及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的关系[9]。
考古学文化分期反映了该文化纵向的阶段性发展,它应该从各类遗存、尤其是器物群自身演化轨迹中归纳得出;它不同于历史分期,不能简单套用文献史学的时代划分给考古材料贴标签。考古分期须详略兼顾:略者要反映文化在宏观方面的大转变;详者要反映文化在微观方面的细部变化。秦器物群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了突变,但此前、此后又表现为连续性的渐变。陈平先生对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析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她的两大器群、五期、十组的分法基本上照顾到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10]。
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同时还要和文献记载中移风易俗的革新运动相联系,惟其如此,才能知其所以然,也才能找到考古学和史学的契合点。秦孝公迁都咸阳,奋起变革,大批关东客卿人才涌入关中,加上战争掳掠,关东青铜文化随之而至。大量新器物的涌现使战国中期秦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几乎改变了原有主体文化因素的构成。如果不是传统屈肢葬和文献记载的缘故,如果是对待史前文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代之而兴起了。秦文化的独特道路对考古学中“文化”、“分期”这类概念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
墓葬分期和等级分类相结合,能揭示社会各阶层平行发展关系以及变动情况,“从而把考古学的分期提高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高度”[11](俞伟超语)。
本书的研究显示:东周时期在东方各国普遍发生的下级僭越使用上级礼制的情况,在秦国并不突出。当东方国家社会急剧变化,推陈出新,礼崩乐坏的时候,秦人却继承酆镐旧习,以掩饰自己的卑微出身,标榜自己属于华夏正统。文字研究也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秦系文字和东土文字虽然都渊于西周文字,但东方文字的变异程度却较秦文字大得多。
3、秦文化的渊源和流向
早在30年代苏秉琦先生整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就意识到屈肢葬墓可能代表“一支早已华化的外族文化”,它所出土的铲脚袋足鬲,“只能向西北去寻找它的渊源线索”。70年代末,俞伟超先生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秦墓所具备的屈肢葬、铲脚袋足鬲、洞室墓三个特征皆来自西北羌戎文化[12];秦人是西戎的一支,但受周文化强烈影响,也可归入周文化这个大文化圈。刘庆柱则明确提出秦文化渊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铲脚袋足鬲和洞室墓并非秦文化的本来特征,而是后来外部文化对它的影响。韩伟就此撰文力图澄清,但矫枉过正,他把屈肢葬这一秦人的标志性特征也一块否定掉了,进而否定“西戎说”。他提出秦文化与殷商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所谓:马家庄宗庙符合“殷人三庙”的记载,秦陵亚字型、中字型大墓与殷墟商王陵相同[13]。见解虽新,其实证据并不充分,“殷人三庙”纯属误传,秦与商陵墓制度的关系应表述为“周承殷制,秦袭周礼”。
与此同时,史学界关于秦人来源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激烈,熊铁基等“西来说”学者认为秦开国前世系为“宗祝伪托”,乃后世伪造,不足征信[14];马非百等“东来说”学者认为《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先世的记载无庸置疑,从地名、信仰都能在文献中找到秦人来自东夷的线索[15]。近年,“东来说”有压倒“西来说”之势。
寻找秦文化渊源,我们认为:必须以东周秦文化为起点,一步步地向前追溯,找到西周秦文化的实物材料,才可作为讨论的基础。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在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发现了西周时的秦文化居址和墓葬,居址可到西周早期,墓葬可到西周中期。赵化成先生分析了其文化因素的构成:一方面屈肢葬、西首葬等葬俗与甘青古文化有关;另一方面陶器的组合形态与周文化有关。对秦文化渊源他持谨慎态度,认为不宜过早下结论[16]。近年牛世山从陶器而非葬俗出发,提出秦文化起源于先周文化,并为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藤铭予更明确指出毛家坪居址最早的陶器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这时的秦文化是先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具体地讲,是郑家坡文化的一支向陇西迁徙的结果[17]。
秦文化起源的探索才刚刚起步,目前亟待在甘肃东部作更多工作,获得新材料以验证诸说。就方法而言,文化渊源和族属问题应分开讨论,因为秦文化不等同于“秦人秦族文化”。即便秦人来自东方,也不能简单地说秦文化来自东方,因为“文化东来说”在考古材料中还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就目前材料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秦文化有多个源头:既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又继承了甘青古文化的因素。探讨文化渊源要抛开单系直线思路。此外,就工作实践而言,要把秦文化从甘肃东部的“西周文化”中剔别出来,还得靠屈肢葬,它在文化渊源探讨中的标志性意义不容轻易否定。
纵观秦文化发展历程,西周中晚期被西戎文化和周文化包围,头角尚未崭露。穆公以后,在与东方半隔绝半封闭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概而言之,反映了其文化上的守旧性。如三晋地区春秋早中期铜鼎的立耳就发展成附耳,秦国在战国早期依然很少见到附耳铜鼎。战国中期秦从东方接受了矮足鼎、锺式圆壶等青铜礼器,从巴蜀吸收了釜、鍪等实用铜容器,创制了蒜头壶等陶器新品种,从北方戎狄部落吸收了洞室墓型,文化面貌发生巨变。随着秦军事力量的扩张,秦文化开始向周边辐射,在影响东方六国文化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异,由此引发的文化碰撞、征服、反抗、融合,为后来汉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目前在河南、湖北、四川等秦国本土之外地区发现的战国中期以后墓葬都有秦文化系统和当地文化系统两类。例如在湖北,既有云梦睡虎地秦人墓,又有鄂城钢厂等楚人后裔墓地;在四川,既有荥经曾家沟、城关镇、青川秦墓,又有涪陵小田溪、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寺等巴蜀文化的墓葬。在上述地区的某些小地点,只有其中的一种,如在河南陕县,秦攻占这里后实行民族清洗政策,把当地魏民统统赶走,“出其人与魏”(《史记·秦本纪》),又从本国迁入居民,使这里只有清一色的秦文化墓葬;在某些小地点,则有两种以上的类型,比如在郑州岗杜。不同种类墓葬的差别到西汉武帝前后才最终消失。可以说,徙民运动在把秦文化传播到各地的同时,也打破了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三晋、楚、巴蜀等几大文化地理单元格局,使他们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得以融合。
4、关于秦都邑、陵墓的研究
史载秦人先祖从中时就居住在犬丘,后来非子被改封在秦,秦人因之得名。秦襄公时前迁都。秦文公至渭之会营建都邑。秦宪公时又迁都平阳。秦德公时迁雍城,这里作为秦国都城时间长达327年之久。后来秦灵公和秦献公又分别把泾阳和栎阳作为临时性都邑,以经略东方,直至孝公徙都咸阳,新都才最终确定下来。秦人次迁都原因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而非其它。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苏秉琦等就对西安三桥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和凤翔县城南的雍城遗址作了勘查。50年代至80年代,考古工作的重心在雍城、栎阳、咸阳。到了90年代,平阳以前的早期都邑的地望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课题。
城市布局形态和城内建筑物的性质功能永远是都城考古的重要内容。先秦很多城市经历了一个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其布局并非一次定型,秦咸阳尤其如此。目前关于咸阳有无外郭城的争议很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依靠考古调查,但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的更新也很必要。咸阳的空间范围是否一直都局限在“山南水北”?能否用六国都城的城、郭分治模式来理解咸阳?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对雍城也该如此。通过考古发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类遗迹是多次人类活动后的结果,我们首先要依据各单位的地层关系和遗物形态去确定其始建年代,不能把不同时期的单位放在一个平面上去探讨其布局。
秦都邑可分三种:一是早期封地,有中心聚落性质,如西犬丘、秦。它们已有代表权力的宫室,如西犬丘有“西垂宫”,秦有“秦川宫”。二是百年以上的长期性都城,如雍城、咸阳。三是为了军事目的设置的短期的临时性都城,如、平阳、泾阳、栎阳。从城市规模也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雍城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咸阳面积最保守估计也有4000万平方米,栎阳却只有400万平方米,城更小,可能不到25万平方米。相差之悬殊,不可以道里计。第一、二种和第三种都城往往共存,如秦文公即位时,还“居西垂宫”;秦献公已“徙治栎阳”,但到秦孝公时才正式把都城从雍城迁至咸阳。
陵墓是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者往往在后者附近。近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就为确定西犬丘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线索。当然,我们也可把陵墓独立出来作纵向考察,秦国陵墓序列完整,特征清晰,在东周列国中实属罕见。从雍城秦公陵园到芷阳东陵、再到秦始皇陵园,茔域界限从兆沟发展成墙垣,封冢从无到有,墓型从中字型到亚字型,从葬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化,以及园寺吏舍的设置等等,一定时期的陵墓形态总是秦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目前秦国和东方列国陵寝制度的横向比较研究尚嫌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晋、楚、齐、鲁等国春秋时的陵墓还没有大宗发现。雍城陵园18座中字型墓被集中在一个外兆包围的茔域内,相互之间没有打破关系,规划严谨,与西周时的北赵晋候墓地,乃至洛阳金村的东周王室墓地有一定相似性;秦始皇陵园布局却和雍城、芷阳陵园有相当差别,表现出很大的跳跃性,其制度渊源似乎更应当到东方国家去寻找。
三考古学思潮的变化和秦文化研究的前景
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思潮此起彼伏,既有奔腾喧嚣的急流,又有水珠飞溅的浪花,很难用一种声音去概括。考古学前进的每一步,既来自于对本学科工作的批判和反思,又得益于其他学科的推动。19世纪中后期考古学产生的原初动力是为了回答“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一时代的核心命题,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哲学为此携手共同作出了贡献。然而,当考古学独立、并与其他学科分道扬镳之后,她却越来越专门化,陷入自身方法论限定的狭隘空间,越来越难以和其他学科对话;当个别学者踏遍某个小地区的每一条溪流河谷,翻遍每一条相关史料,并为此耗尽一生时,考古学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四分五裂了。“真正的学者在地方”,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怀疑由此抬头,60年代宾福德号召的“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的确鼓舞人心,至今余音回荡。学科之间概念相互介入和思想碰撞日益频繁,新进化论就曾为新考古学关于文化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借鉴。本世纪末,一种试图突破人文和自然科学界限,以了解物质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目的的“复杂科学”正在兴起;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思考遗迹遗物所反映古代社会的复杂性问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这种学科大整合的趋势也显露端倪,张光直先生关于破除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之间门规戒律,建设一门“中国先秦史”的倡议[18];俞伟超先生关于下个世纪考古学行将消亡的预言,都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19]。考古学不能只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剩余价值”,也不能只会简单对照民族学中“活的例证”;我们不需要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的“三拼盘”,而是三者的水乳交融,目的是为了回答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一些课题。
研究秦文化对理解世界文化有么意义?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下: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塞维斯(Service)和萨林斯(Salins)倡导新进化论,他提出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的区别是:前者指物种或文化系统对特定环境的专门化适应,后者指更高级形式生命的出现或文化综合水平的阶段性提高。二者存在逆反关系:一个物种或文化系统越是专化和适应,它走向更高等级序列的潜力就越小。进化运动的总体特征是非线形的,一个发达了的物种不会必然导致下一个进化新等级[20]。秦帝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更高形式的国家形态,然而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秦国的发展速度却大大落后于东方国家;商鞅变法成为转折点,此后经济上突飞猛进,军事上一跃成为头号强国。秦发展史再一次证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直接引进先进社会的文化,跳跃既定阶段,赶超那些貌似繁荣、但实际发展已频临极限的国家。这就是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落伍者的特权”。
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落后国家没有沉重的传统包袱,引进新装备时不必就淘汰旧设备付出太大代价,因而具有广泛的适应力和潜在活力。秦民质朴,这在墓葬材料中看得很清楚:不严格遵守棺椁制度,洞室墓率先在他们中间流行;庶民坚持日用陶器随葬的习惯;铜礼器制作粗糙草率;秦系文字较六国文字简便易行等等。春秋以来秦对周礼的模仿仅仅停留在物质表面,没有深入到精神内部;仅仅局限在上流贵族,没有普及到社会下层。秦入主关中后,周遗民的向背对巩固其统治举足轻重,故利用周礼名号,标榜自己华夏族的血统,以暗合当日现实。战国中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又很快将之抛开。通观秦国青铜文化的发展,战国中期两大器物群交替之际的不衔接不整合现象,实可称为一个文化的断裂,这在东方国家根本看不到。商鞅变法是列国变法运动中最后一个,但最为彻底、最富成效。正因为民风淳朴,法令得以上行下效;正因为还不象六国那样公室衰微、政归私门,国君才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变革。荀子谈到秦国强大的原因,也说:“入境观其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荀子·强国》)。
从葬圭习俗的变化也可以观察秦人对周礼的态度。《周礼·考工记·玉人》把圭的使用放在首位,天子册封、诸侯朝觐、使者征伐、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以及祖先宗庙都要用到,是重要的瑞节礼器。从周成王削桐叶为圭封唐叔虞的故事,可知圭在周人心目中更是赐国拜官授爵的信物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公、侯、伯之类高级贵族才配拥有,象子、男爵位的只能“守谷璧”或“守蒲璧”。正由于贵重,在西周时期较大的周人墓中才能见到圭。沣西张家坡发掘的182座小型西周墓葬,仅出土2件石圭,就很说明问题。相反,在西周中晚期的小型秦墓中随葬石圭却极普遍,甘谷毛家坪8座西周秦墓座座出圭,多者10件,少者1件,“石圭出土时多散置于死者身上,估计原放在棺盖上”。它们多用页岩或板岩打磨而成,不同于玉圭,它们不可能是礼仪生活的实用品,当专为随葬而被制作,有祈求来世高爵厚的意义,这反映秦人已经认同周礼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但对其等级制度的遵循又远不如周人严格。春秋秦墓葬圭习俗依然盛行,如宝鸡福临堡11座墓,凡出铜陶器物的皆有石圭;长武上孟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20座墓出石圭110件;凤翔高庄战国中期以前的墓共出石圭77件。此时,东方国家的小型墓也开始用石圭随葬,侯马上马墓地244座墓,出土各种质地的圭680多件,大有泛滥的趋势。侯马还曾发现制作石圭的作坊遗址,原来尊贵的礼器现在沦落到可以滥制贱卖的地步,礼制被僭越被破坏自不待言。令人感兴趣的是,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墓里葬圭之风嘎然而止,西安半坡112座、大荔朝邑26座、河南三门峡公布的150座秦墓中没有出土一件石圭。如此大的转变说明了什么?这与秦墓原来流行的彩绘仿铜陶礼器和微型化的铜礼器在战国中期被日用器皿完全取代的现象有着相同的意义。商鞅变法推行的社会大变革使人们把周礼那一套价值观及其符号系统彻底抛弃;奖励耕战、崇尚军功,秦国之俗变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要略》)。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晚期东方国家葬圭之风依旧,50年代在洛阳烧沟发掘的59座战国小型墓,每墓出土一件石圭。由此可见,对周礼的破坏,秦和东方列国走过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秦文化的考古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七十年的时间,光阴荏苒,当年稚气未脱的少年今天已成为耄耋长者,秦文化研究前进的每一步,不正象征着中国考古学成长的蹒跚脚步吗?忆往昔,思来者,如果说30年代秦文化的发现肇始于中国学者对探索本国文化起源的一种执着追求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把秦文化研究回归到中国文明的总体进程中去,如何理解秦文化所走过的独特道路和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则是新一代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任务。
发表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引用请查核原文。
来源丨先秦秦汉史(文/梁云)
(责任编辑:张云文)